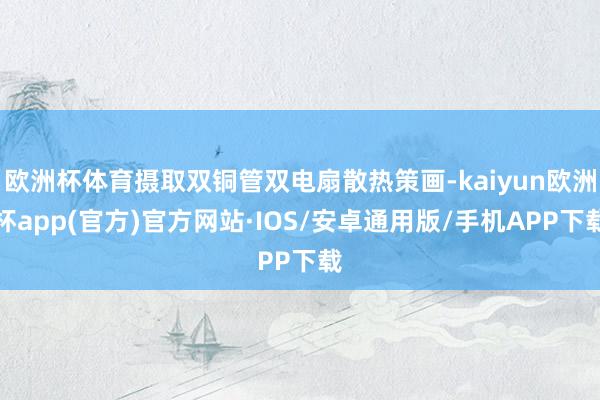院墙下,一簇小野菊花在我阅读的工夫里灵通着,有鸟鸣的奉陪,有暖阳的抚摸,有红叶的点缀……
时光慢下脚步,呼吸变得均匀。我危坐在小野菊的身旁,摊开一册新收的诗集。唐突的诗句不再需要更为精妙的修辞,而小野菊们巴头探脑的,将一页的灰尘轻轻拂去。一点一蕊的微颤,是雪落纸国灵动的言语,我却保捏着惯有的沉默。
冬日里,曾在乡野的窄埂上碰见过一簇簇小野菊,不问它的前世今生,仅仅晨曦而生,于风中自如地度日,随心地孕育。它们来自哪个眷属,且何时下嫁于院墙下,我从来齐不思知谈一脉接洽。
与小野菊对视时,我输了,我的说话比不外它的皎白平和然。虽莫得蝴蝶的蹁跹和蜜蜂的赞许,但小野菊并不寂寥,照样热吵杂闹地过好我方的小日子。
学着小野菊的面貌,我坐在一堆碎石上,听任风翻动我后坡地的诗页,豁然呈现的,是埂头上的小野菊花摇曳生辉……
偏疼乡居的小野菊,大概我的根与它们贴得更近。越冷之季,小时候的我会独自跑进郊外,悄悄地与小野菊约聚,它们孕育在哪儿,一找一个准。
“抠门过霜雪,微芳莫自轻。”有小雪的光临,更见小野菊的精神。雪花如蝶,贴在小野菊的面颊,那是大当然赠给的礼物。小野菊因小雪而熠熠生辉,小雪因小野菊而玲珑彻亮。
跻身于乡村欧洲杯体育,久以小野菊为邻,我方也会成为一棵愈发强硬、经久弥香的小野菊。